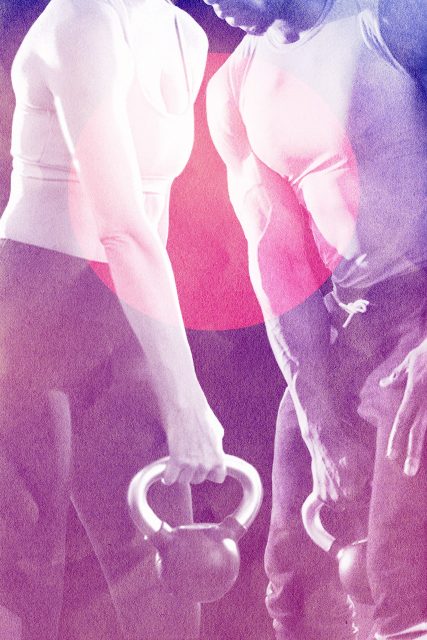我繼續在 WhatsApp 上查看是否可以找到他的任何痕跡,看到他對上一次上線時間是12:37,他把浣熊頭像換成了一個小孩於母親在海灘上的照片。 我找到了他的Instagram,但是依舊處於不公開狀態。他的 Twitter 是公開的,但自2016年以來他再也沒有發布過任何東西。我用 Google 搜索他的名字,然後大學報刊的 Facebook 帖子出現,因為他顯然曾經是那裏的編輯。我找到了他的 LinkedIn 個人資料,然後他穿着淡藍色襯衫的照片出現,我立即關閉了該頁面,因為這意味着他會收到通知,通知他我剛剛查看了他的個人資料。
「我將頁面關閉得這麼快,或許他不會知道我看過他資料?」我通過電話問朋友。「我關閉了網頁,因為 Reddit 上的某人說,這樣做將使 LinkedIn 不再知道我的IP地址,因此他們將不會收到在其個人資料上顯示的帳戶持有人姓名,不會收到通知。 或者,如果他們這樣做了,就像是『人們一直在查看你的個人資料…』,而不是我的真實姓名。」
我的朋友發出 “Mmhmm” 的聲音,聽起來好像她在認真聽。但是我可以從輕微的緊張中看出,她的電話塞在下巴和肩膀之間,因此她可以專心做其他事情。
「薄荷醇,請。」我聽到她的耳語,然後傳來一聲嘶叫聲。
「你在做什麼?」
「我在商店。」
「那麼你覺得呢?」我問。
「謝謝。」她對店主說,然後對我講話,這一次我可以知道她才將電話握在手裏面。「你為什麼還迷戀這個人? 你不是和他約會一樣嗎?」
她是對的——這不重要。 我只認識他六個小時,沒見過他的家人、朋友。我沒和他做愛,我沒有告訴他我的秘密。
Mary Gaitskill 在她的新書《Lost Cat》中談到了哀悼失去別人不認為值得哀悼的事物是怎樣一回事。當她那獨眼灰色虎斑貓 Gattino 失踪時,她把傳單放到路燈柱上,搭好陷阱,晚上大喊貓的名字,把滿頭大汗的衣服放在花園的籬笆上,希望他聞到後會回來。但是當她告訴人們自己的損失時,他們認為她過分緊張及誇張了。
「哦,那是你的創傷,對嗎?」當 Gaitskill 告訴他正在經歷的事情時,男人這樣回應。
她回答:「是的,這是一種創傷。 你可以說他很不友善。 你可以說我很傻。 你可以說他很老套。 你可以說我很虛弱。」
我在社交隔離這段時間感到很無聊,花了大部分時間與父母一起看狗,還經歷了長時間的休息,幫助決定用哪種石頭重做花園。我有這麼多時間去思考,而我常常最終還是想到了他。
我們夏天見了面。他既是老師又是足球運動員,他寫詩,而且太火辣了,他看起來像是一本少年雜誌的插曲。我們坐在長椅上交談,直到附近塔樓的光把我們和周圍的一切投射成黃色。談話是如此輕鬆,以至於有些事情從我的嘴裡冒出來,以至於我都不知道我在想甚麼,這些事情會讓他點頭並說「誰說的?」然後我告訴他:「我自己想出來的,」但也有可能是我在某處看到的。我告訴他 Eve Babitz 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儘管我懷疑她的書是他所感興趣的,但他還是在電話記錄中寫下了她的名字。他說他來自的小鎮在海邊,我以為他撞到水裏,波濤拍打着他的胸部。他在公交車站候的車亭裏親吻我,說:「你或我的住處」,我說「不是這次」,因為我以為今次可以嘗試一些其他東西。
但隨後,聊天逐漸從段落變為未完成的句子,再到兩個寂寞的藍色剔號。
過了一會兒,我停止談論他了。但是幾個月後,他又給我傳送了消息。
「我們為什麼停止發送消息哈哈?」
我假裝不知道為什麼。然後我們聊了一段時間,談論了其他事情,例如《 Succession》有多精彩,花式番茄醬似乎從來沒有 Heinz 那麼好。
但是隨後他承認了一點:「我可能真的沒有安全感。」
看到他的回覆,我感到很溫暖。我想他確實喜歡我,實際上,他是如此喜歡我,以至於他在我身邊實在是一件痛苦的事。我說了很多令他自卑的聰明話。
為了證實這一點是正確的,我告訴朋友 Henry:「你見過某人並感到『哇,她是如此完美,我根本無法跟她約會?』」
「不,那不是問題,」Henry回答道。「我曾幻想過人們,但由於害怕別人會怎麼想而承認自己太尷尬,於是就死了。我有時也會感到無聊,然後又變得飢渴,所以再次發出信息。然後想知道我為什麼這樣做。」
幾天后,老師停止了回覆。
我本來應該聳聳肩,說「男人是垃圾」,然後繼續前進,但是感覺就像我要分手了。在超市裏,我會記得我們親吻時他嘴中的薄荷味,以及它與我的唇彩的草莓味混合的感覺。在床上,我想起他繫鞋帶時如何用厚臉皮的微笑抬頭看着我,陽光從他的鼻樑上湧現,也許我不應該在那灌木叢中生氣? 也許他遇見了某人? 有時我會夢見他在和朋友們一起嬉戲,他的嘴越來越大,直到變成鯊魚般的大小,笑聲從他尖銳的牙齒間散發出來。當我和寫大學論文的其他編輯一起找到他的照片時,我感到很高興,因為他的髮型真的很糟糕。
上次分手後,我哭了幾個小時,朋友們一直陪着我。當他們不被打擾時,他們和我一起晚上出去玩。 但是顯然沒有人會給予同樣的關注。 我想告訴他,要求見面,但他絕對沒有欠我任何東西。
誰來決定甚麼值得哀悼? 我和前任在一起很多年,即使轉過身也能分辨出他正在做什麼樣的面部表情。所以當他離開時,我很想念他,就像失去了肋骨般。 我不會這樣想念老師,因為他在我世界的時間沒有足夠長。但這是痛苦的一種特殊形式,我很清楚失去機會,我一直想知道在他溫暖的胸膛上入睡會是什麼樣子,知道他要上樓梯了,因為我甚至沒有想過要記住他走路的節奏。和我的前任一起,我們嘗試了,但失敗了。和老師在一起,我們甚至沒有嘗試。
我給我一段時間沒有聊過天的朋友發了訊息,以了解她在這段社交隔離時期的狀況。 「沒關係,」她說。「說實話,我只是有點累了。」事實證明,她在 Hinge上與他聊天的一個月左右已停止回复。 他們本來想去散步,她還特別為此購買了這款價格過高的Kangol毛絨水桶帽,但是,當她建議了確切日期時,他卻沒有出現。
她說到:「我知道這很愚蠢。」
「別這麼說。」我答到,然後我們繼續聊下去,因為有時正是愚蠢的事情,才真正傷人。
原文轉載自 British Vogue
Editor
Annie LordCredit
Cover Image:Photo Courtesy of Westend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