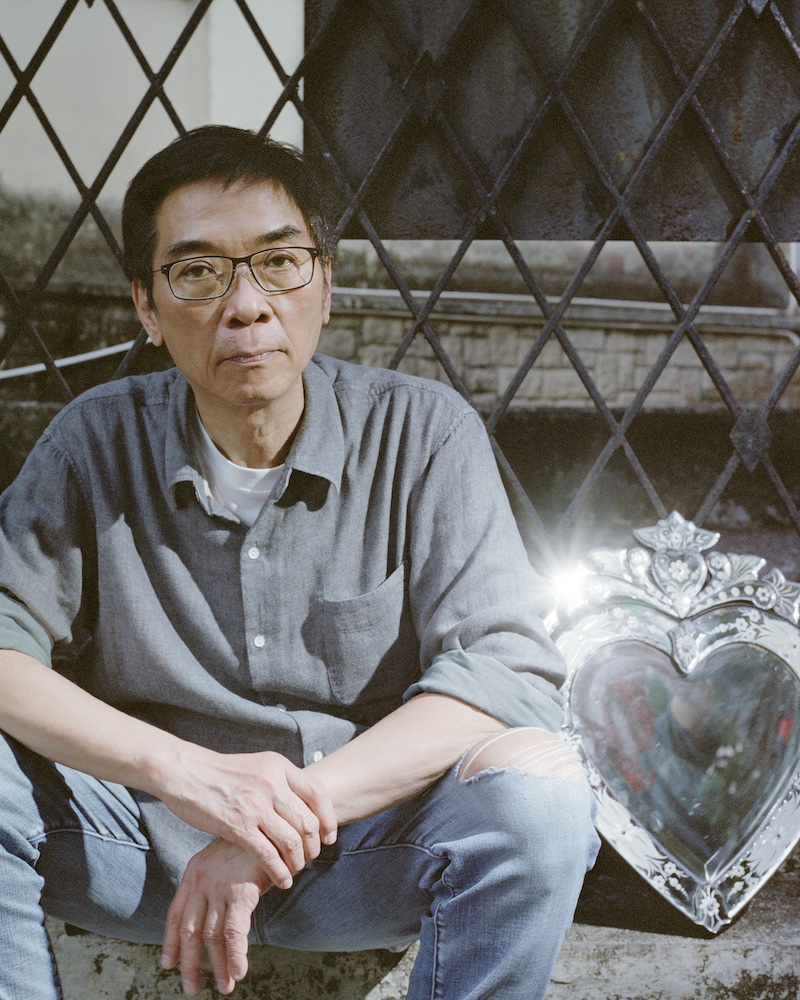Anais:早前 Tzusing 成功在 Kiko Kostadinov 的平台上推出新曲 《Balkanize》,想知道這次合作是怎樣誕生的?
Tzusing: Kiko Kostadinov 他們一直有來我在倫敦的演出。我合作的唱片廠牌 PAN,也剛好跟他們有合作關 係。原定去年五月到韓國舉行 Kiko Kostadinov / Pan 派對,計劃因大流行告吹。 Kiko Kostadinov 發布新網站時,邀請了 Pan 製作一些內容。我想,這是個不錯的地方,來發表我將於年底推出的新專輯裏的其中一曲。
Anais:第一次聽到你首張專輯《東方不敗》;那閃閃發光的敲擊音效,殺氣騰騰的震動——驚為天人。武林與音域之間的無畏、無邊,竟然通電了。是什麼啟發你音樂裏傾瀉而下的戲劇性?
Tzusing:不是所有人都會喜歡看見燎原烈火吧(笑)?音樂是創作人的情緒表達,而這種焦炙正是我所熟悉的。我喜歡這樣暴躁、進擊的狀態。我也喜歡其他不同的情感,只是這樣令我感覺更自然,或者說,最與生俱來。製作這類型的音樂,也許是在面對自己社恐的影子,是一種宣洩。這聽起來讓我好像個狂妄的瘋子,但其實我是個挺容易相處、詼諧又頑皮的人。
Anais:初中某天在家發現了《藍宇》VCD—— 迷上封面的映像;然而當時抱着大概是「長大後才看吧」的念頭。 後來遇到《藍宇》電影文本《劇本簿》,方便上課時在抽屜裏追看,心裏一直澎澎澎澎!好幾年後,終於有機會看到電影,《藍宇》仍是讓我最沉溺的愛情故事之一。你認為亞洲⻘年的反叛精神,是否都很少以搖旗吶喊的方式表達出來?
關錦鵬:於我而言,創作的動力來自不安比憤怒更多,我是通過作品去轉化這種情感。比如拍了《藍宇》,別人會說:「你為同志發聲啊!」我會認為,不要一直覺得自己是 Minority。甚至那些「最懂女人心」,或是同志電影導演云云的標籤,拜託通通拿走它們。假如我在拍第一套電影就遇上《藍宇》,說不定,會動不動就為誰請命。回想,我覺得拍電影四十年,有這十一部作品的關錦鵬,也有份該不去搖旗吶喊啊。
Anais:上海時裝週讓我最為悸動的瞬間之一,少不得在 Club All 看 Tzusing 的演出。某程度上,與工作夥伴們身陷如此鼓躁吶喊的空間,是一種時尚體制的顛覆。當中包括來自⻄方的編輯、買手、網紅,跟地球這端的設計師和創作人。你與時裝的關係是怎樣的?你怎樣看俱樂部文化,和它在國內其他文化領域的影響力?
Tzusing:這個問題挺廣泛的,哈哈。我享受時裝。我覺得,人們透過時裝表達的概念,總是更容易與大眾產生共鳴。相比起傳統藝術,或是我所來自的音樂領域。現在,俱樂部成為了志同道合者碰面的地方;好比年代遠去 的咖啡廳。當然不是隨便任何的夜店,它必須要有非常清晰的審美取向。俱樂部提供了分享新想法的空間,讓想法相近的設計師、藝術家或音樂人即時地交流;創作過程很多都是從群體間互相學習,和反饋演化而成的。
Anais:關導演的紀錄片《男生女相》,是場特別尖銳的對話。從討論邵氏時期的劍客開始,你跟侯孝賢、楊德昌聊父親的距離感,問張國榮是不是自戀、陳凱歌是不是恐同;其中訪問徐克的部分,很咄咄逼人(笑)你說: 「雖然《東方不敗》以同性疑雲陣陣作起跑點,卻在異性戀才是唯一的前提下跑完全程」。陰柔與剛陽種種議題, 在眼前的時裝世界依然沸騰;華語世界裏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中性角色?
關錦鵬:在我媽那一代,深信任劍輝、白雪仙匹配到不成。即使明知任劍輝是女人,但一穿起古裝唱粵曲,她們就把自己投射到白雪仙身上。有次任劍輝在電視上演女角色,我媽會衝口而出問:「她為什麼扮女人?」譬如 《胭脂扣》裏面的如花,梅艷芳她有一種俗艷,不能夠說是「靚女」。大家都愛說「百變梅艷芳」,我們也因此給她好多「面貌」——淡妝、濃妝、開場所打扮成男裝與張國榮對唱,是對接下來纏綿緋惻的愛情故事的一種挑釁。
Anais:後來我和關導演經常在大坑喝酒時碰面。有次你「三更夜半」從朋友家飯局過來,帶著主人做的湯圓讓 大家嚐嚐 — 原來那是林⻘霞的手藝。有機會把 TZUSING 的《東方不敗》介紹給她,猜她有什麼感覺呢?
關錦鵬:我覺得林⻘霞是很 open minded的人,我們也會適時交換一下好聽的音樂啊。(從IG上再了解一 下 TZUSING 的音樂)或者我年輕的時候,也就差不多躁動。
Anais: Tzusing 為 CAV EMPT 製作的 MIXTAPE 裏放了林憶蓮的《三更夜半》!你童年的華語流行曲體驗是怎樣的?
Tzusing:我在新加坡長大,又常到台灣探望我的祖父母,所以國語流行曲總是徘徊在附近。我記得高凌風的歌,但是從來未曾投入過,也徹底沒有喜歡過他。潘美辰讓我十分着迷,而且我仍然是李宗盛的鐵粉。
Anais:聽說早期,你從不少王家衛電影裏採樣(SAMPLING),然後運用到 Trip Hop 的場境中。半年前你曾來過香港,今天的城市面貌,和你影像裏的記憶有什麼對比?
Tzusing:的確,有不少香港面貌都被電影浪漫化了——說得通,因為它們與城市的喧囂有着截然的碰撞。很多香港電影主題,都是圍繞着階級之差,和拼命奮鬥的人。在香港,我真切地感受到這些歷史的影子。我愛在狹小的城市裏,感受海量的文化共冶一爐。即使不一定能彼此相諧,我享受眼前這一切,排山倒海的並列在街上。那節奏、密集性、還有空間的不足,都是獨一無二的,即便是與上海這樣的城市比較;我既樂此不疲,又感覺高不可攀。
Anais:關導演在《阮玲玉》裏面說到「做資料」的部分很帥!當時你飛到上海,從翻閱老照片、舊書,到張羅一些絕跡人物進行採訪。九十年代初,你所接觸到的老上海演藝圈怎樣看香港電影?
關錦鵬:九十年代初,上海的默片時代演藝圈,年紀已經很大。他們知道我拍過《胭脂扣》,但是對香港電影新浪潮不特別了解,說不定心裏想,拍出來就是一般傳統人物傳記。演員黎莉莉、陳燕燕等一代女明星,還有幾乎已經無法說話的導演孫瑜,接受訪問時,《阮玲玉》劇本尚未成形,所以完全不知道電影會以什麼型式面世。很純粹,一說到三十年代的上海電影,好渴望分享自己所記住的輝煌、一起拍戲的快樂,有種驕傲和感恩。
Anais:開拍《越快樂越墮落》之前,你與邱淑貞見面一個半小時,她便講了三十分鐘電話;所以電影中她飾演的 Moon 和 Rosa 兩個角色都十分愛講電話。今天手機動詞從「講」變成了「滑」,你與網絡世界的關係是怎樣的?
關錦鵬:當然她有一直say sorry。好像剛才有朋友發訊息過來,我最低限度也習慣錄語音回覆,能夠有空間的話就直接回電話去。朋友之間聽見大家的聲音很重要。對我來說電話就是聲音,聲音令人有幻想,有可能收到這條語音的他正在赤身泡浴呢;反而視像電話就不可能了,我不那麼喜歡。
Anais:Tzusing 把 Instagram 用得很跳脫獨到。有次,你轉發了一系列假冒陳冠希求網友「微信轉賬300 塊」的語音訊息,原來是他自己的二次創作。你的分享總是同時滲透著幽默、聲音和身份認同的想像。
Tzusing:(笑)謝謝!我沒有很活躍地經營它什麼的。我是單純分享令我感興趣的東⻄,那或許反映了我關注的一些議題。那個陳冠希微信求助的梗太妙了。從他的ABC口音,整件事的光怪陸離;這種荒誕的幽默,或是淋漓盡致的超現實,我想,音樂創作似乎也是異曲同工。大家都不過是渴望抽身於日常,然後發笑一下而已。
Anais:新浪潮語境下創作的《阮玲玉》以劇情片結合紀錄片 ——三十年代的「阮玲玉」與張曼玉自己對角色表達看法的片段相互穿插。非要以 Netflix 用語說明的話,形式就像 Terrace House 鏡頭一轉,主持人們也像觀眾,面對劇情你一言、我一語的。關導演看過現在流行的真人綜藝節目嗎?
關錦鵬:拍攝《阮玲玉》時期的張曼玉有一種理直氣壯。最近就有跟林奕華聊起《乘風破浪的姐姐》裏面所呈現出某些演員的狀態,有點難過。當然,有話題性才能得到收視, 應該說「點擊」才對。聽說爾冬陞在《演員請就位》很火爆,這樣便讓人想看一下。我也當過《我就是演員》的評審,帶著導演的身份參與真人節目製作,最希望能夠做到的是善待演員。
Anais:大流行下,音樂創作對 Tzusing來說有什麼改變?你站在「直播演出」的哪一方?
Tzusing:一般來說,每年我會巡迴到歐洲大約三次,同時走訪亞洲各個地區,但疫情期間這一切只好叫停。空出來在家做音樂的時間,剛好逼我把專注力都集中在完成新專輯上。這段時間我完全沒有做過直播演出。那消失的群眾、朋友、音響、氛圍,我卻跟朋友們一直在玩《APEX英雄》呢。
Anais:記得我們有次心血來潮,在家做《胭脂扣》「放映會」嗎?聽關導演說起往事「聲音導航」— 彷如置身 「雙聲道」之中。我想,就如電影似是愛情片,也可以是關於「你我他」穿越時空的故事。此刻你最想點播梅姐那一首歌?
關錦鵬:這很有意思,曾經許多年前我把《抱緊眼前人》播給我的另一半聽(靜)我恨不得此刻就回到去那個最Indulge(沉溺)的關錦鵬年代。
>> 立即訂閱電子書及紙本實體書click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