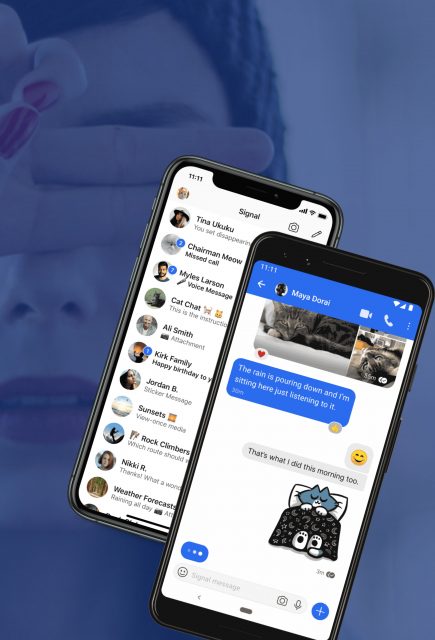每一個社交媒體平台的開始都是很無辜的。 Twitter是一個提供突發新聞和時事進步觀點的地方。 Facebook是一個與朋友和家人分享個人照片和更新的方式。最初,Instagram根本不是關於個人的,它是一個精美的藝術、風格和攝影的視覺平台。雖然每一個都保留了它們卑微的初衷元素,但過去十年的社交媒體已經暴露出了它不屈不撓的黑暗面。 Twitter已經成為仇恨言論和部落主義的平台。 Facebook的數據隱私政策在多個場合受到質疑,與公司和政黨交易我們的細節。 Instagram屢次被選為年輕人心理健康最差的應用,因為它所宣傳的不切實際的美和成功的代表,不僅僅是由那些有償的影響者所宣傳的,而是由大多數想要向同齡人投射「最好的自己」的用戶所宣傳的。
關於社交媒體對年輕人的影響,目前已有大型群組研究,例如 JAMA Psychiatry研究觀察6600名美國青少年,發現每天花在社交媒體上的時間超過3小時的人,更容易產生焦慮和憂鬱。 Elsevier 發表的一項針對1.6萬名中國青少年的研究同樣將開屏幕時間的增加與抑鬱症聯繫在一起,作者評論說,這些數據代表了 「一個重大的公共健康問題」。在英國,61%的11至21歲女孩表示,她們覺得自己需要看起來 「完美」(Girl’s Attitudes Survey)。然而,這類研究往往告訴我們我們已經知道的事情,自己已經親身經歷了多年。很難得出關於社交媒體究竟是如何影響我們行為的量化數據,因為該技術仍然是如此之新和不斷發展,但有一些廣泛的可識別的主題已經成為我們一代人經驗的特徵。
這些主題將總結2010年代我們對社交媒體的經歷
1. 我們受到了更多的刺激,但這也削弱了我們的關注度
還記得那種叫做無聊的感覺嗎?當你不得不站在隊列中或者坐在牙醫的等候室裡。現在只有當你的手機沒電了,附近又沒有充電器時,才會真正發生這種感覺。更俗稱為恐慌。
在過去的20年裡,人類的注意力已經下降到8秒,比金魚還少。通知、無限滾動、自動播放和吸引人的、色彩鮮豔的應用設計已經嚴重影響了我們的注意力。
「有證據表明,只要身邊有一部智能手機,就很難集中註意力,即使在你不主動使用手機的時候也是如此。」位於舊金山的社會心理學家Erin Vogel說。
正如前Google設計倫理學家、矽谷叛逆者Tristan Harris在他的TED演講《How a handful of tech companies control billions of minds every day(少數科技公司如何控制每天數十億人的思想)》中所解釋的那樣,社交媒體的設計是利用說服性心理學來讓我們回頭看更多。被稱為 「注意力經濟」,應用程序之間相互爭奪消費者的時間。而品牌總是贏家。
「我的注意力被打亂了,」社交媒體專家Natasha Slee說,她領導媒體品牌的社交策略和內容創作。 「那張Douglas Coupland「我懷念我的前互聯網大腦」海報讓我產生了很大的共鳴。我懷念在拿起手機滾動的反射動作之前的時間空隙裡我所做的事情。被動地消費手機上的內容,讓我們失去了可以花在周圍環境中的時間,也失去了可以在現實生活中互相交流的時間。我總是在想,如果沒有手機,生活會是什麼樣子:我會更聰明嗎?我的關係會更好嗎?我會更健康嗎?更有教養?」
2. 我們自我物化,包括我們的容貌和生活。
我們不僅根據一系列的圖片來判斷別人,決定是關注、取消關注、喜歡還是滾動過去,我們也學會了從外部來判斷自己。我們是否表現得很成功?是否善於交際?吸引人嗎?能否讓人 “喜歡”?我們找出自己最可賣的部分,在社交媒體上向同齡人做廣告,這種方式對上一代人來說似乎很不自然。 「Instagram把我們塑造成了迷你品牌和自己生活的視覺日記本。」Slee評論道。
這種以別人會看到的方式來看待自己,以別人會評判自己的方式來評判自己的行為被稱為自我物化。專門研究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心理學家Dr Helen Sharpe解釋道。 「自我客體化來自於對象化,也就是你作為一個個體的價值和價值純粹基於你的身體。因為你意識到你的價值是基於你的身體,所以你會受到其他人的監視,所以基本上他們都在看著你,以計算出你的價值是什麼,隨著時間的推移,你會將這種經驗內化,所以你在自我監視,不斷地觀察自己,以確保你是盡可能的「有價值」。這與社交媒體以及你可以描繪一個版本的自己的想法超級契合。」
3. 我們做著同樣的夢,我們要的是同樣的東西
社交媒體在慶祝視覺生活方式、可上Instagram的服裝和迷人的職業時,呈現了一種狹隘的成功生活觀。辦公室工作、在醫院工作、教書,沒有什麼是可以上Instagram的;而下一代人的願望則直接證實了這種影響。在聯盟營銷網絡AWIN向一群英國11到16歲的孩子提出的 「你長大後想做什麼 」的問題中,”Social Media Influencer “和 “YouTuber “是第二和第三選擇。根據《2019年Indian Kids Digital Insights》,73%使用社交媒體的兒童會要求父母給他們購買他們看到的兒童影響者的廣告產品。而在 Channel News Asia一篇題為「青少年追逐社交媒體喜歡的危險[潛伏]」的長篇閱讀中,一位新加坡家長描述了抓住她的五歲孩子在鏡子裡模仿一個vlogger說:「點擊這裡訂閱。點擊這裡查看更多內容。」
我們不可能都成為有影響力的人,YouTubers和#GirlBoss,擁有超級成功的副業。隨著所有關於努力成為最好的人和追隨你的夢想的勵志名言的發布,社交媒體可能會讓我們感到更有雄心壯志,但它也產生了巨大的壓力,要求我們成為卓越的人——特別是在一個數字驗證的職業內。
4. 積極的一面是:我們已經發現了集體力量。
從積極的一面來看,社交媒體增強了我們的能力。我們已經意識到,人數是有力量的,我們現在有能力與他人聯繫,首先是為了讓我們感覺不那麼孤獨,其次是為了實現改變。
「看到全球黑人女性社區在Instagram上的活躍,驗證了我的存在,如果沒有我在社交媒體上欽佩的女性不斷提醒,我想我永遠無法理解。」Lynette Nylander說,她是一名創意和編輯內容顧問。
從網上的LGBTQ+社區,到身體積極運動和#MeToo,社交媒體創造了一種團結的感覺,並促成了一種集體力量。它讓我們能夠相互教育,相互倡導,促進了社區意識。它讓沉默的人們發出了聲音。
那麼,我們該何去何從?
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人是社交媒體的小白鼠。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裡,潮流開始轉變。聲勢浩大的矽谷叛逆者越來越多。 Facebook和Instagram終於做出了一些努力,進行了一些試驗,比如取消可見的讚。寫文章和帖子撕毀自己 「完美 」生活帷幕的影響者越來越多。 「在某個地方,我想我開始把可分享的自己看成是真實的自己,並把任何可能威脅到可喜歡性的傾向埋藏在內心深處,我甚至忘記了它們的存在。」Tavi Gevinson在The Cut上發表的一篇題為「如果沒有Instagram,我會是誰?」的自述中寫道。
當我們開始意識到社交媒體賣給我們的夢想生活可能並不那麼美好時,我們可以開始重新認識到作為自由思考的個體,而不是沉迷於內容的消費者,我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Vogel充滿希望。 「當適度使用時,社交媒體對大多數用戶來說,幫助大於傷害。我不認為它永遠不會是一種完全積極的體驗,但它確實有好處。」她還指出,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幫助我們弄清楚什麼時候社交媒體是有害的,什麼時候是無害的(甚至是有益的)」。
Slee說,她 「只能看到它隨著下一代的發展而發展。社交媒體已經深深紮根於我們的文化中,超越了手機上的應用,我無法想像它在未來十年內消失」。她希望各平台對其設計的上癮性負責。
2010年代是測試期。如果為社交媒體提供動力的技術能夠以某種方式開發出一種良知,有可能使用人工智能,如果用戶能夠為他們的自我宣傳帖子和刻薄的推文可能對他人產生的影響承擔個人責任,那麼2020年代可能是社會快速改革的十年。前提是如果。
原文出自:Vogue Paris
Editor
SARAH RAPHA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