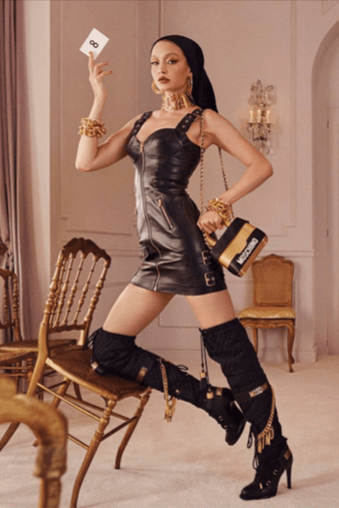你很難找到比「當代母親處境」更引發兩極討論的話題。儘管如 Angela Garbes《Like a Mother》、Leslie Jamison《Splinters》與 Amanda Hess《Second Life》等在近期推出的作品,都在為所謂的「媽媽戰爭」提供了珍貴視角與細膩辨析,但若想體驗理智上的崩潰,就只需要參與一些關於「傳統主婦」的辯論。
在疫情危機餘波未平、孕產與自閉症錯誤資訊氾濫,以及社會對婦女兒童的保障還沒有得到全面落實的當下,母親們的處境普遍不容樂觀。這也就不奇怪於近年電影對母愛的描繪,總是浸染着如此濃重的絕望色彩了。
Charlize Theron in "Tully", 2018. Photo courtesy of Everett Collection
中產母親的精神困境
曾幾何時,母親的不快樂猶如文化論述中的高壓線,是無人敢輕易觸碰的禁忌。然而從《Tully》(2018)、《Nightbitch》(2025)到《If I Had Legs I’d Kick You》,這些作品不約而同描繪生活優渥的白人母親們,因缺乏實質或情感支持而被逼至崩潰邊緣,更運用超現實元素強化張力,無論是 Charlize Theron 飾演的 Marlo 幻想亟需的家務幫手,或 Amy Adams 演繹的壓力爆表的居家藝術家母親竟變化為犬。而 Lynne Ramsay 即將推出的《Die, My Love》由 Jennifer Lawrence 詮釋深受產後抑鬱所苦、漸陷精神失常的新手母親,勢將為此脈絡再添力作。
沉默的母親
然而這些絕非當下母親故事的全貌。Alice Diop 執導的《Saint Omer》(2022)無疑是近年最撼動人心的典例,故事圍繞懷孕作家旁聽塞內加爾女性被控殺嬰的審判過程。影片拒絕提供簡單解答,沒有預設論點或「生育令人瘋狂」的制式敘事,唯有一位立於母親這個角色門檻的女性,在他人悲劇中窺見自身的倒影。「《Saint Omer》的關鍵在於沉默,」Jennifer Padjemi 在 2024 年 Criterion Collection 專文寫道:「它傳遞恐懼、憤怒、共鳴、孤寂與悲傷,更訴說着世代女性從未獲准傾訴的創傷。」
體制壓迫下的母性掙扎
有別於《Tully》中 Marlo 或《Nightbitch》裏母親的困境,在《A Thousand and One》中,Teyana Taylor 飾演的單親媽媽 Inez 所面臨的母親危機源自外在社會,而非內心掙扎。電影開場,剛出獄的 Inez 從寄養機構中帶走年幼的兒子 Terry,鏡頭隨後記錄她在虐待、警察暴力與體制性歧視的夾縫中奮力守護親子關係的歷程。在毫無社會安全網的處境下,幻想的保姆或「犬模式」街頭狂奔對她而言根本是種奢望。

Taylor as Inez and Aaron Kingsley Adetola in "A Thousand and One", 2023. Photo courtesy of Focus Features
母親的跨世代對話
Pedro Almodóvar 的《Parallel Mothers》(2021)為當代母親的困境賦予了深厚的歷史角度。影片雖聚焦攝影師 Janis( Penélope Cruz 飾)與少女單親媽媽 Ana(Milena Smit飾):兩人在同日分娩後命運交織——但 Almodóvar 同時將西班牙內戰的歷史陰影編織其中,讓新生母親的疼痛與孤獨,在歷史創傷的脈絡中產生迴響。
母愛的雙重本性
即便在 Pixar 動畫世界裏,對母親形象的刻畫也日趨深刻。Domee Shi 榮獲奧斯卡的 2018 年動畫短片《Bao》,圍繞一位年華漸逝的華裔加拿大母親展開:當親生兒子長大離家後,她將有生命的包子視作情感寄託。影片高潮處,母親含淚吞下包子男孩以免其離開的場景,深刻捕捉了當代社會對母親認知的重要轉變:即使身處動畫的世界,頌揚育兒的美好與深刻亦不再需要迴避其中的艱辛與痛楚。電影與現實同樣告訴我們,這兩者本就可以並存。
原文轉載自《VOGUE》美國版
Editor
Emma Specter